【西电校友】专访53级校友雷达对抗专家张锡祥院士
编者按:为了深入实施大学文化建设计划,加强与广大校友的联系,不断增进校友与母校的沟通和交流,凝聚校友力量,传递母校情感,扩大校友影响,提升学校声誉,在校长基金特别支持下,由党委宣传部、校友总会、学生工作处等单位联合,日前正式启动了面向各行各业优秀西电人的专访工作。这一专访工作是继“西电往事”之后,学校在讲好西电故事、传承西电精神方面推出的第二个重要策划。为此,我们特开设“西电校友”栏目,对专访内容进行刊载。欢迎广大师生为本栏目提供采访线索,联系邮箱:news@mail.xidian.edu.cn,联系电话:81891719。
一腔热血保家卫国 半个世纪情系雷达
——专访53级校友、雷达对抗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锡祥
■ 文字整理/特约记者 王朱丹
2015年4月11日,西电校友工作组一行赴成都专访了53级校友、雷达对抗专家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锡祥,以下为采访内容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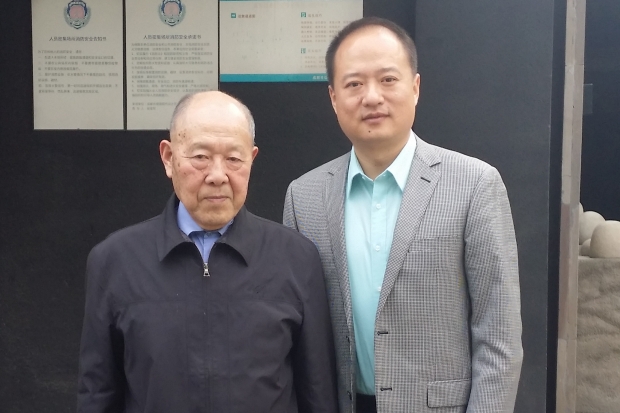
张锡祥院士与专访组成员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肖刚合影
坎坷少年求学路:四门考试三门满分
记者:张院士您好,非常高兴能够采访您。请给我介绍一下,您是在怎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?
张锡祥:我出生于1933年。我曾祖父那一辈从河南逃荒到山西当长工,就在山西成了家,生了我祖父他们兄弟四个,早年去世了两个,就剩下祖父他们兄弟两人,一个是在张家口做生意,一个是在家管家,生活条件属于中上等的水平。
我的父辈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两人。父亲跟着祖父在张家口做生意,伯父在老家。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干得很好,但是他那时染上了抽大烟,就被老板解雇了。那个时候村里面年轻人抽大烟的很多,几乎属于普遍现象。父亲回到老家后开始做些皮影戏工作,但在那期间仍然抽大烟,不断地卖家里的地,后来在1936年左右,伯父跟父亲分了家。我祖母当时跟着父亲过,因为她是亲生母亲,也责骂我父亲抽大烟不争气。我母亲是非常普通的家庭妇女,常常偷偷的哭也不敢讲什么。当时还有一个舆论,说抽大烟的人用不了几年就得卖儿卖女换钱买大烟,所以当时其他同龄的小孩也常常讥笑我和姐姐,说我们肯定过不了几年就要被卖掉了。
后来到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。1937年底,来了八路军,在农村建立了新政府,叫抗日人民民主政府。新政府当时有两项重要工作,一项是宣传抗日,另外一项就是改造抽大烟的。他们把抽大烟的人集中在一起,戒烟后才放行,大概集中了三个月后,大部分人都戒了烟。我父亲出来后,就又去了张家口原来做生意的地方,中间仅回来过两次。1944年他回来那次,在路上得了伤寒病,持续发高烧一个星期后就去世了,家里面就剩下了祖母、母亲、我和我姐姐四个人,我们就只能依靠地里面的收入维持生活。
记者:您能跟我们说说您少年时代的求学经历吗?
张锡祥:我从1939年开始在村里上小学,直到1945年。这期间城里被日本人占领,成立了县政府。农村里面是八路军成立的抗日人民民主政府。我们一边念日本人要求的语文、算数,一边偷偷的念八路军发的宣传抗日的书。那时村里很缺劳力,因为中青年男子都参加八路军去了,所以学校里只有冬天上课,一到夏天,老师、学生都要回家种地。
到了1947年,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,八路军的野战部队就撤去保卫延安。我们躲在家里,根本不敢在外面活动,生怕被抓去当兵。我那时14岁,当时抓兵名义上要求是18岁,但实际上他不管年龄,只量个子,身高超过1.5米就给抓走了。1947年的秋后,我们村有一个老师在文水中学教书,当时的兵役制是只要上了中学就可以不用去当兵,所以我和三个同学就一起跑到了那里,实际上并不是去念书,而是为了避免被国民党抓去当兵。
刚到文水中学时一切还算平静,但到了1948年初的时候,就开始搞自白转生运动,这个运动的含义就是让原来八路军所占领地域上的人们,向他们交代以前都给八路军干过什么事,还要保证以后绝不给八路军干任何事,实际上就是划清界限。我们四个同学是从农村来的,我们村叫东堡村,离云周西村约三华里。刘胡兰在1947年1月12日牺牲后毛主席为她题词:“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”,从此刘胡兰的名字在解放区是家喻户晓,闫锡山的兵称云周西村为“小延安”。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是八路军的人,是八路军的侦探,对我们四个人进行了三个月的严刑拷打,将四个人分开,一人分别住在一间房里,分别审问我们到底是不是八路军派来的侦探,上的刑法包括坐老虎凳、压杠子,我们才都是14、15岁的小孩子,确实为躲避勾子军的抓兵而到文水中学的,打了我们三个月,也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是八路军的侦探。后来由老师做担保,说我们都是家里的独子,怕被抓去当兵才来到这里的,就这样我们才被放了出来。
记者:您的经历,我们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,太残酷了。之后您又去了什么地方继续求学呢?
张锡祥:1948年夏天,文水县全境解放了。秋后文水中学就开学了,通知我们村的四个同学再去上解放后的文水中学读书。我们又上了解放后的文水中学,老师知道我们曾受到过严刑拷打,对我们几个都很关心。上了一个多月的课,学校就推荐我们到农村去搞土改,直到1949年5月土改才结束,文水中学和汾阳中学合并,那时我也没去汾阳中学上学就回家了,在7月份跟着一个亲戚去了北京。
到北京后,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中学在招生,然后就报名,结果就考上了。于是,我就在1949年9月1日正式开始上初一,那年我16岁。当时那个中学的名字是民国中学,是国民党时期的一个私立学校。那时候,我除了吃饭睡觉之外的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,在学校一次考试中,四门课我考了三个100分,一个99分,一下子在学校出了名,从那以后,我整个人都自信起来了。
冬天放寒假时,我也没有回家。一方面从北京回山西太远了,另一方面也为了省路费,当时我念书每个月大概七块钱伙食费,都是亲戚资助的。那个寒假,我就一个人在宿舍里自学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学完了初一下学期和初二上学期的课程,后来就考了插班生,跳级到北京劳动中学,读初二下学期。三年初中我只用了两年时间,于1951年夏天毕业。
初中毕业了以后,我本来是想考火车司机的,后来看到国家号召抗美援朝参军,我就报名参军了,完全没有跟家里商量。一两天后就获知被批准了,我们一批人就在北大集中,被运到了张家口ZYJW工校,先进行了五个月的政治学习,解决生活观、生死观问题。后来考上预科,上了雷达系。
八年西电专业学习:搞研究必须养成连续的思路
记者:当时是5年制,您为何在学校生活了8年呢?
张锡祥:到了军委工校,我们政治学习用了半年,然后经过考试,被分为报务、预科和工程系三个等级进行正式学习。上过大学的,还被直接抽调出来当了老师。因为之前我上过初中,就被分到了预科班学习。1953年,预科学习完毕,我开始正式就读工程班雷达系。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正式以培养雷达技术人才为目标的雷达专业。我所在的班级叫534班,也就是53年入学的4系的意思。
当时是五年制,我们这个班本应该是1958年毕业,但那时学校刚好要从张家口搬到西安,在搬迁前学校安排我们去南京720雷达厂实习,学习雷达整个的加工过程,等实习完了以后我们就没有回张家口,而是直接去了西安,在1959年4月正式毕业。
记者:从张家口到西安,您在学校学习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如何度过的?
张锡祥:到了西安以后,我们参加了半年的工厂实习,我是在西安的786厂,也就是黄河厂实习。当时,我在那里搞了一个小课题,叫做“雷达的惯性跟踪”。这个课题要解决的问题是:当雷达跟踪目标过程中,如果丢失了目标,天线还应该继续按照原来的速度和方向,再跟踪上20-30秒钟。
为了做好这个课题,我们经常是住在实验室,也不回宿舍,晚上连夜干,太累了就在桌子上趴着睡一觉。大约1个星期左右,课题就有点眉目了,知道该如何入手了。这段经历告诉我:从事科学研究,如果连续不间断,效率能够提高好几倍。就像你连续一个星期思考一个问题,一定比断断续续想上两三个月的效果都要好。停下来去干别的事情,思想不连续,回头还得重新开始!要想搞专业、搞科研,必须养成连续的思路。
记得当时我做实习课题的时候,思想一直处于不间断的状态,除了睡觉之外,连吃饭、走路都在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当然也有人问累不累,我没有正面回答他,而是反问到:你们打麻将整夜整夜地打累不累?我和你们一样,你们对麻将入迷,我对课题入迷。只是入迷的对象不一样,没别的什么区别!总之,我始终觉得,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,除了有责任心外,还必须要有浓厚的兴趣,而且兴趣要到入迷的程度!
在实习期间我还做了别的课题,指导我的老师对我很满意,他认为我是所有同学中毕业设计做得最好的,我记得这个老师找我谈了三次,希望我能留在他们厂里工作,我说我是军人,是要服从组织分配的。后来在四月份时,我被分配到了北京机关通讯兵部,在雷达连当兵,做DZDK方面的工作。
记者:在长达八年的求学生涯,您印象最深刻的事都有哪些?
张锡祥:首先是教师都非常有名、都很敬业。当时,给我们上专业课的都是非常有名的教师。他们有的是参军后调到军委工校的,有的是大学毕业了直接留校任教的,还有的是从浙江大学、中山大学等名校调过来的。在张家口,周围环境比不上大城市,条件还很艰苦,这些教师却从来没有因为从大城市到了山沟而闹情绪。当时雷达还是新兴学科,除了毕德显院士外,好多老师都没有学过这门课程。因此,在专业课学习过程中,毕德显院士亲自给我们讲雷达原理,丁鹭飞教授给我们上雷达实习,保铮院士给我们讲脉冲技术,蔡希尧教授也给我们上过课。名师授课,终身受益,他们渊博的知识,敬业的精神让学生佩服不已!
其次,当时的军事课印象也很深。给我们上军事课的是国共战争期间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,他们接受过正规的军事理论训练,而且还有实际战役的指挥经历。因为朝鲜正在打仗,所以我们的军事课,都是从实战出发,从最基础的班进攻开始,连排进攻,一直到师团进攻。课堂上,教师模拟给你配备炮兵、坦克、飞机,教你如何排兵布阵,军事课学习得很有意思。这段军事课学习的经历,对我后来从事电子战研究有很大的帮助。因为打仗不完全是技术问题,它必须和战术结合才行!
军事课学习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。一天晚上,我们被紧急拉到张家口的野外,然后被告知根据所学知识自己寻找回学校的路。张家口的野外,没有任何可供使用的工具,分辨不清方向和距离,我们只得通过星星的位置、甚至是树木的长势确定方向,摸黑往学校赶。从理论到实践,从实践到实战,这就是张家口军委工校的学习方式,这对于我一生的学习、工作都有很大的影响。
第三就是张家口期间的学习条件。我们是预科班,按照当时的军委工校学生分类,算是年级最低的。我们居住在西山坡,曾经是日本人的骑兵营,条件很艰苦,学生住的是9个人连在一起的大通铺,教室是养马的马棚。虽然马棚安上窗,但房子还是四处漏风,我们只得自己动手把漏风的地方糊起来。上课时,房子里面虽然也有一个小火炉子,但还是冷得很。印象最深刻的就是,上课记笔记,记着记着墨水就会结冰冻上,只得用嘴巴呵上几口热气,才能够融化了继续记!上预科的后期才由西山坡搬到东山坡,虽然东山坡也很艰苦,但比西山坡好多了。
从事雷达工作一辈子:西电的影响是决定性的
记者:您刚参加工作时的情形时什么样的?
张锡祥:我在北京当兵半年后,那时国家要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,要进行KJ检阅演习,一个师的KJ排队起飞,编队飞行,我们就在雷达显示器上看他们编队飞行目标回波信号很是壮观,这是在学校看不到的。我下连当兵,相当于操纵员或者雷达维护技师的工作,使我收获很大。
当兵回来以后,我就正式开始做DZDK工作了。记得当时从苏联进口了几个地对空的干扰机,体积特别大,大概需要三个拖车才能够拉走,而且我们手上什么资料也没有,更没有任何培训,唯一有的就是一个说明书,全是俄文。领导给我们的任务是三个月后要把这些机器开动起来。我们起初感到非常困难,就一点点的钻研,后来还真成功了。通过那一段时间,我的业务技能有了很大提高。
后来从苏联来了三个专家,他们培训了西电的几位老师,在西电成立了第一个DZDK班。在1960年下半年,苏联专家撤走了,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培训班该如何办下去?由谁来代替苏联专家?就在这个时候,领导安排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和一个同事一起,将培训班的任务接了下来。后来大家的反响还都很好。
苏联专家撤走了,我们又研究了一个操作训练模拟器,孙俊人部长很满意的,他说想不到我们司令部参谋里面,还能搞出这么高级的模拟训练器,就说要将这样的人送到研究所去,不应该留在机关里面。所以我就被调到了国防科工委第×研究院×所的DZDK研究室。
到了1965年,DZDK研究室被从×所抽出来,来到四川变成了现在的研究所。所以说,我从毕业以后,工作虽然换过几个地方,但是所从事的专业一直没变。到了研究所后,我所做的课题,最后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一、二、三等奖都有,以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。
记者:您是著名的雷达专家,您一生从事的工作和您在西电曾经接受的教育有什么样的联系?
张锡祥:西电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。
总结一句话:如果当初没有上西电,我现在可能就只是个火车司机。当时我准备考司机培训班,都已经考了一门了。后来才抗美援朝参军,参军后才又逐渐的上了雷达专业,那是一个转折点。
现在想想,当时在张家口学习的热情为什么那么高呢?原因是最初去那里是要准备拼命打仗的,可是到了之后发现,不但不用拼命上战场,而且还是管吃管穿的学知识,心里头非常满意,特别珍惜,所以学习特别卖劲儿。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知道雷达这个词语,也是从那时开始,我这一生都没有离开过雷达事业。
记者:您在几十年的雷达对抗工作中,主要取得了那些成就?
张锡祥:因为保密的关系很多不好讲,这一方面我用成果来说明,获得国家级的奖3个,省部级的奖7、8个。
情系母校发展:要重视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
记者:您对现在高等教育有怎样的建议?
张锡祥:大学里面一定要重基础。想当年,我们是5年制的,数学、物理、专业基础都学得非常扎实。现在虽然也有4年,但是学习外语花费的时间太多,还得留出半年时间找工作,和以前相比,充其量算是2年半制的。
我和高校来往频繁,我发现学生学习外语的时间太多,甚至占用了大学的三分之一左右,这个问题值得商榷。当时我们上大学时,学的是俄语,不过目标很明确,就是能够借助字典看得懂本专业的书籍,所以我们学习外语占用的时间非常少,从而留出了大量时间认真学习专业基础。
当前,我们国家大学生的确比较多,但是还有一个问题,那就是具有国际水平、顶尖水平的学生却太少!对比一下当年的教育和现在的教育,也就容易找到问题的症结。当时的大学生,要实打实地学5年专业技术基础,因此创新能力强;而现在虽然是四年制,实际上顶多认真学了两年多专业知识。这个问题,责任既不在学校,也不在学生,而是国家教育体制的问题!
我个人的观点是,中学、小学可以学习外语,大学外语应该是选修,愿意继续学习的你就学,不愿意学得太深的,有了以前的基础也就可以了,应该把时间尽量花在专业基础或技术基础的学习上。毕竟,我们每年出国的、去外企工作的学生,那是少数,充其量有10%。因此,为什么一定要让90%的人跟着10%的脚步跑呢?
现在不是50年代,每年大学生只有2-3万人;现在每年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,只要有40-50万对英语很精通,也就足够了!外语要好、又能够发表SCI论文、还能够进行技术创新,这些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实现,是极不合理的。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,不可能什么都会!
大一点说,一个群体,只有有了分工合作,才是真正的高水平团队!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会,那是低效率的群体。记得在《恰同学少年》中,讲到毛泽东主席的学习方法时,就有一个观点:由四个在各自领域的顶尖专才组成的团队,那是高水平的教学团队;四个什么都会一点的人组成的教学团队,那是一个普通的团队!
因此,现在教育体制对英语的要求是极不合理的;要求每年600多万的学生都过四级、过六级,也是极不合理的!实际上,自主创新能力和外语水平的高低并不大,却和专业基础、研究思路的关系很密切。要知道,并不是外语好,创新能力就强!因此,我建议高校对外语的要求要放宽些!
记者:今天的西电正处于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的关键时期,作为校友和专家,您对学校的建设发展有哪些建议?
张锡祥:学校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发扬西电的优良传统,这个决不能丢。
第一个方面,我觉得还是要重视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,西电在这方面比别的学校有优势。当年在张家口条件那么差的情况下,我们培养出来四个院士,这个成绩在行业里比清华、北大都好。现在工程院一个学部里,西电毕业的年轻院士比较多,同一个组里,西电人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大。这些人的发展过程,都离不开在西电所受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影响。
第二个方面,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。学生们将来毕业后,不管是做技术、搞创业、经商,还是继续深造进行科学研究,德智体这三个要求有一个不满足,都会出问题。虽然现在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但是这三个要求我觉得始终没变。
第三个方面,是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。我记得我们上学时,老师会留一些选做题,鼓励大家主动思考,举一反三。现在有好多学生不知道如何思考,老师讲了的会,没讲的就不会,这在科学研究方面是绝对不行的,因为科研的对象都是未知的,未知是要在已知的基础上发展出来,所以独立思考能力应该在学校时就注重培养。
记者:您对年轻人的发展有什么建议?
张锡祥:对于年轻人的发展,我的建议是选择一门专业,就要一直坚持下去。我的一生有两个特点,一是在西电学了八年的专业基础知识。另一个就是在工作的50多年中,工作单位变过,但是专业从没变过。
我分析了一下,工作中实际上是有1/3的时间是在学新东西,20年里面就等于又学了6年,这些时间可以积累很多的知识。年轻人要想搞成一件事,就要一心一意,攻克困难,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流专业人才。
(本次专访组成员: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肖刚、研究生教育管理办公室主任卢毅)
成长过程中的回忆
张锡祥
吕梁窑洞记忆深,马棚教室能育人。
东山坡上办大学,培养多批高材生。
为国为民创新品,建设祖国万事新。
国家兴旺又发达,帝国主义不敢攻。
鸦片战争成历史,祖国远洋全球行。
人君有志遍地花,不看形式看内容。
【三点说明】
1、成长过程的回忆:(1)吕梁窑洞记忆深,指我在1948年12月至1949年5月在牛家垣村搞土改时,住的是窑洞。(2)马棚教室能育人,指我在张家口预科学习时,是马棚改的教室。(3)人君有志遍地花,指的是人若有志气,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能搞出成绩来。
2、勾子军是闫锡山的兵,他们到村后就抢粮抓壮丁,老百姓给他们起外号称“勾子军”。在1948年春,勾子军搞的“自由转生”运动,为什么把我们东堡村去的四个同学,进行了三个月的严刑拷打。因为我们东堡村离云周西村很近,约3华里。1947年1月12日刘胡兰牺牲了,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“生的伟大,死的光荣”以后,在当时的解放区大为宣传刘胡兰的英勇事迹。勾子军称云周西村是“小延安”。她活着的时候我们都见过,她的年岁与我们差不多,死的时候还不满15周岁,只比我大7个月。因此勾子军怀疑我们村去的四个人是八路军派去的“侦探”。因此,对我们四人进行了三个月的严刑拷打,最后没有找到任何证据,找保了事。
3、学校推荐我搞土改:因为当时1948年冬,在我们那里区县干部很缺,要支援三大战役、支援解放太原、要筹建南下工作团,又要搞土改。因此,政府号召学生,本人自愿,学校推荐。我们村的四个同学都自愿报名参加土改,我们经过半个月的土改培训后,我被分配到牛家垣村搞土改工作。


